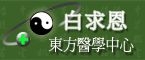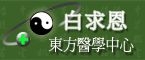鲜花( 5)  鸡蛋( 0)
|
本帖最后由 Acup2 于 2018-8-20 12:29 编辑
! ~2 l- I6 m3 O5 M# g: }7 M p$ E* ~2 F$ L, V; H$ E+ B
经方和时方的区别" ^# P$ \* s8 v
9 ^" u2 k: |& I& [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,由最初的单方、验方逐渐积累发展演变,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理论体系。如今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广的有经方与时方两大理论体系。本文所指的经方是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方药理论,时方是指以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等为理论体系的医学流派。9 t ]) `; N; n
1 ^# a9 p; N4 _$ u
经方的核心理论是方证对应,其中《伤寒论》以六经为纲以方证为目,论述了所有疾病发生的基本脉证规律与治则方药,是中医辨证治疗学的总论,而《金匮要略》是以杂病为纲以方证为目,属于各论。临证的着眼点是疾病所表现出的特异性的脉证组合,强调方与证的严格对应。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处处展现的是这样严谨的方证对应关系,即有是证,用是方。方证辨证在临床中并不注重气虚血瘀、肝郁肾虚等,大论中极少有病机术语。虽“罕言病理”,但并非没有病理,经方方药之中蕴含独特的理法。( E# J, q' O+ B
" J/ `/ m) A8 G" q- \5 M# |时方的核心理论是以阴阳五行、脏象、经络、运气等学说为主要内容。这一流派的影响最为深远,成为历代中医的主体。从汉唐到明清,绝大部分的中医典籍,均属时方体系,如《华佗神医秘传》、钱乙《小儿药证直诀》、张元素《医学启源》、张景岳《景岳全书》、陈士铎《辨证录》等。这一流派的临证思维特点是,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,判断其气血阴阳盛衰,脏腑虚实等,辨出其相应的病机,进而确定治法,拟定方药。时方中的泻白散、左金丸、导赤散、龙胆泻肝汤等方名即已显示其思维特征。时方在临床上强调对每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,晚近的中医更重视辨病治疗,甚至结合西医的病理药理来指导用药。
! s# V' h. _) u6 }: A9 t+ h5 x4 [* L- M5 x; i7 ?7 _" ^" ], J& V: G, g
经方派与时方派对药物的认识亦有很多区别。时方尤其到金元以后,对药物的认识更繁杂,如“十八反”、“十九畏”等,而经方中的附子粳米汤等,恰恰就是附子与半夏同用。. M7 w; k: [5 o& o# n% a. K
1 D, w: \2 {# Q* f4 q, Z
时方治病常面面俱到,方大药杂;而经方常单刀直入,击中要害,药简效宏。时方辨证相对主观笼统,经方辨证则更客观精确。
' O& s5 t! [* O C, L; z. ]1 z6 p* d0 H- t5 ]8 c' R
虽然张仲景被称为“医圣”,又常以“效如桴鼓”来形容经方的疗效,但为什么经方的普及不尽如人意?我们认为自金代成无己首开以《黄帝内经》解《伤寒论》以来,《伤寒论》的真实面目已被扭曲,严重阻碍了人们对《伤寒论》的认识理解。从近现代来看,曹颖甫、吴佩衡、胡希恕、范中林等可谓纯正的经方家。' `7 J* g# N( D F+ E2 a
5 `0 V3 a+ j, {2 `& ^5 ]9 S谭杰中:
0 Z5 w+ e! p* P8 A+ { o D' p2 }- e+ A8 M5 E- f8 A
中医分为经方派、时方派,这,不但中国人晓得,日本人也晓得。经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古方派」,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后世方派」,意思一样。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,也都晓得,经方派和时方派的「分水岭」是什么──那就是所谓的「金元四大家」。「金元四大家」虽然齐名并称,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,并不是同生同死。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,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,就是张元素,也就是张洁古(易水先生,易老)。而,张洁古做了一件「功德盖世,罪恶滔天」的事情,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。而那件事情,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「归经理论」──某某药入某脏某腑、哪一条或哪几件经。
& t8 ]" Y' j+ D) B3 S: G/ _: d7 X# }7 `7 z$ T4 p |/ b/ k! A6 ]
归经理论是错的吗?不能算错,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,临床上也大大有用,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,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,对学习中医者而言,是甚有帮助的。但,它是对的吗?也并不全对。因为,它大大地「窄化」了一味药的药性。% B) S M1 v! m* Q9 P2 c
. R! `" G; w4 J1 D同样是用中药,以「《神农本草经》、张仲景(或《汤液经法》的作者)所知道的药理学」创出来的方叫作「经方」,汉朝到唐宋,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。而以「归经理论」创出来的方,就叫「时方」,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,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。最古的《神农本草经》,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「性.味」,也就是「什么味道」、「温凉寒热如何」,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,则是「稍微提及」,例入「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」,不是通盘性的认同。而其后,魏晋的《名医别录》,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、《日华子本草》、《海药本草》、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,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《证类》、《大观》二本草……等诸多书籍,大都只是顺着《神农本草经》之后补入新发现的「效能」,却未曾对「本草理论」作更多的理论分析。
0 ?& B$ |, v) o; r9 i
. R- l4 K- m+ S+ e A. D% v( `, p5 t到了张洁古,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,发现到「太阳病病到太阳、阳明之间时,会用到『葛根』这味药……」,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:「葛根是阳明引经药,如果感冒太早用了,反而会引邪入阳明!」同样,对于柴胡,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,说它会「引邪入少阳」(明.李中梓),而至于桂枝,因为有帖「桂枝汤」是治「太阳病」的第一主方,于是「桂枝」的归经也就变成是「太阳经药」了。石膏,他也说是「大寒之药,不可轻用」。& t# ?( b& P5 E% q- ?% R7 q
/ F0 d2 h+ Z2 r6 u5 Q# X# T
这,有没有错?从某个角度来说,复方「桂枝汤」的确是「会」作用在太阳经,而单味药的柴胡、葛根和少阳、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。可是问题就在于:「不只如此而已!」后世的学者,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,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,可是却变成「见树不见林」,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。
, }# J4 [$ J" t( f$ x) }
- N# w* l) H& Z6 C& @8 a可是,因为这种「时方药理学」方便好用又好记,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,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「金元四大家」,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,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,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「补中益气汤」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《妇人良方》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「去男人下阴臊臭」专方的「东垣龙胆泻肝汤」,都是其中的佼佼者,也堪称「伟大之方」。+ J+ C5 L7 d5 d$ ?( J8 c% s1 Q9 i1 _7 l: l
; p( L0 t4 J6 o" k& q3 D) q! }( ?可是,归经理论,却是一套「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」的不完全的理论。洁古本人、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《内经》起家的,偏得还不太多,但愈用到后来,纰漏愈大,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,「一剂知,二剂已」变成了今日的「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,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!」到了后来,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,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「末法」劣化状况,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《神农本草经》,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。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
" a" i0 U& l( i$ K6 {0 r% c4 T( l$ m$ S- l* E
明朝那一位「把之前有的理论、药性全都收录」而编成《本草纲目》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,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。源头在张元素。光是他以降的几句「葛根引邪入阳明」,「柴胡引邪入少阳」,「石膏大寒不可轻用」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。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,太阳初感,证齐全了,就可以用葛根汤;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,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,石膏更只是「凉」而已,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,很难显出药性。可是张元素之后,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,绝大部份的医者,小心翼翼地就都「尽量不要用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方」了。5 g2 i( H5 g5 x
直到清朝,事情才有了转机。如果以医术而论,陈修园、徐灵胎等人,因为临床功力够,其著作《神农本草经读》或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都有卓然不群之见,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,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。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,主要的功劳,其实起自「儒家」。清代的儒家,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「革命活动」,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,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,朱熹乱改原文,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;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,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。可是,总觉得有问题。但,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,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,要如何平反才是?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:「用同时代的文献,做平行比对!」比如说《论语》中的某个字,朱熹说是这个意思,可是先秦时代的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等其它书中出现这个字时,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,于是他们就晓得:那是朱熹弄错了,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。比如说「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」的「习」字,先秦当时是「实践」之意才对(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『学到上手、会用』的意思,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),「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,很快乐。」如照朱熹的说法,学了就一直温习,就会快乐了吗?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?2 G& t+ m; N/ A4 v) A' k& J: I) H
7 Y8 K+ g2 ] c; L* t h$ F
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,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(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),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,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,是:明.卢之颐《本草乘雅半偈》→清.刘若金《本草述》→清末.邹澍《本经疏证》→清末.周岩《本草思辨录》。邹澍在《本经疏证》以及周岩《本草思辨录》用了「平行比对」的方式来批注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,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「只要『证』合,药投下去,一定会好」,总有效率达到「神的绝对领域」的《伤寒杂病论》(用其它的书也不行,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,未到『绝对领域』,比对会出错)。他用「减法」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,比如说,《伤寒论》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,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,于是,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,就可以得到「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」之结论。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,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,慢慢减来减去,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……
, I) {7 U. V E T* G7 y/ | }# y8 Q9 R6 C4 g2 |0 x! N
这样一点一点的「相减」,彷佛在玩「数独游戏」,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……而结果,说也奇怪!减出的一句一句,竟恰恰就符合了《神农本草经》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,于是,「三贲」(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)之一的《本草经》之谜,就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绝对领域之谜,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,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!、1 o4 r/ i3 \" S' q3 ?
8 G4 j6 V( T- J: \2 N- c
如果有些药味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,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,却也趋近于「绝对领域」的孙药王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等书,再去配合《伤寒杂病论》,一味一味相减,做分析……这种苦工,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,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,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,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。
I/ z; z) X8 `) O$ M8 J7 }+ X( S; [' x$ V8 }' d% U# k
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,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。容川的理论,其《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》中《本草问答》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,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,实堪与润安先生的《本经疏证》相互辉映,其金木药性相反、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,与敦煌出土的《辅行诀》竟然是相通的。中医的大秘密「古典药理学」,终于在清朝的最后,得以重见天日。所以,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,可以说是很幸福的。
9 X( i4 j3 V- C% \! u y2 ~/ v1 o6 b5 |0 X& G# u
至于「时方药理学」呢?果真是害人之物吗?有时,我也觉得很难论断,或许该说是「看个人」或「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」吧……(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,都学会了就会超强,也就是说,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,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,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?)% Z. ?1 X% v8 n: |$ D- _
: r6 `+ d& D1 U" o3 R( J
有一位时方大家,他创的方剂,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。如果仲景可称为「医圣」的话,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「医仙」了吧。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,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(傅山),他的《傅青主男女科》也是家庭常备好书,尤其是妇女病,自己在家翻书吃药,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。(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)
# f6 g5 f8 \: m0 L2 X" D8 O
" J0 N) t& B; {7 ]1 r6 u* `0 u9 E [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,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,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,依此事实,如果换成今日,恽子愉前辈的「看西医检验报告、透视片」来开中药,彭弈竣先生的「不开经方」、皮沙士先生的「平易之方」却也都其效如神,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,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。真的是「看个人」。
3 W2 @8 f5 [$ ? |
|